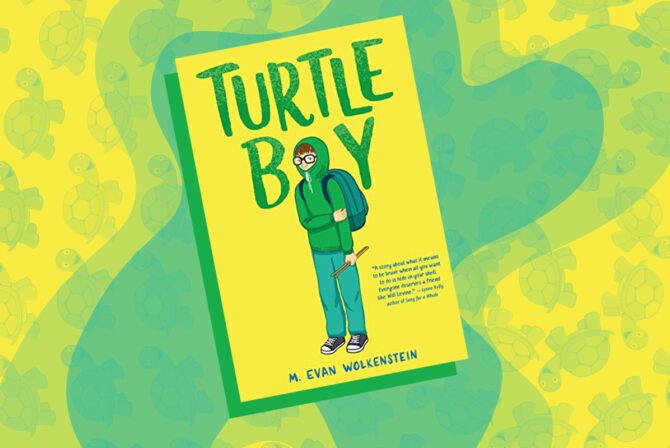我庆祝我的39岁生日在医院套件与我的丈夫他的第二次开颅手术前一天晚上。我们点燃了我们的汗水蜡烛,并责令医院准备的鱼片。由于道格的癫痫发作,我们不能喝酒,所以我们举杯同佩里耶品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在道格的最后几个月里战斗了脑瘤,他和我谈财政,埋葬与火葬,我怎么能找到丈夫谁将会是一个伟大的父亲给我们的儿子。
“太糟糕了拉比的拍摄,”道格说。
道格升至天主教徒,他感觉到,我想再婚有人犹太人,尽管我从来没有阐述它。
虽然道格容忍我安息日蜡烛寺会员,他不同意我的热情文化试金石。他从来没有在奥斯卡根植于犹太编剧,像我一样;他不喜欢“安妮·霍尔”。
他还拒绝在犹太教的实质性的表情,像BRIS为我们的儿子。
“更安全的医院,”他决定和关于他们包皮环切。
我的丈夫开始搜寻道格去世三个月后。我的朋友警告我,这是太早不管我正在考虑。我告诉他们,我开始在此之前,道格哀悼一年后,他突然中风,失去了短期记忆,并且有他的大脑里取出的一部分。
道格去世后,我渴望什么,我知道,这是道格。
周六晚上,特别是,我错过了拉进车库晚饭后出来,让熟悉的对话与人我爱的乐趣。
“你把垃圾在吗?”
“不。我以为你做到了。”
这些琐碎的交汇处,所以毫无意义的,安慰的回忆,是救助独自拖着有人罐。
我们的恋情开始于大学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感到异国情调。他已经乘坐大巴盘,并通过高中球童;我倒是只夏季工作在日营。他曾提出在玉米面和小德比糕点小吃,食品妈妈永远不会允许在家里,要是她知道它们是什么。
我第一次遇见他的祖父母,他的祖母 - 谁连他的父母莫名其妙地称为“保姆式” - 看着我说,“你知道,她可冒充意大利“。
我横梁。
我的祖母不能说反转,约道格提醒她一个犹太男孩。道格看上去像的Hans Brinker与白的金发,绿眼睛,一个运动员的身材,和永远红润的脸颊。(面颊很可能是酒渣鼻,不过我更愿意想象他与冰鞋池塘。)
他可以睡,直到下午1。如果我睡得那么晚,我的父母都会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很佩服他的家人如何冷静是,相比于我的。我的父母kvelled关于好成绩,但他们还徘徊,曾经坚持认为大学的朋友接我,宾州车站,因为他们不想让我独自走在长岛铁路。
道格的父母很少给恭维,他们没有眨眼,他吹嘘在靠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酒吧桶一夜行驶在斯古吉尔曲线之后。
道格英年早逝,但至少他并不害怕住。
“照顾彼此照顾,”他的母亲对我们说,我们留在欧洲经过六周前的蜜月。
我们有酒店预订仅一周;道格说,我们会找出从付费电话,其余列车车厂 - 这是1987年的,毕竟,智能手机不久。
“不会是有意义的节省你的婚礼的钱?”妈妈问。
当然,还有我们的不同的并发症,我无法预见。一个月我们结婚之前,例如,我受伤了,当道格选择了与他的朋友在滑雪之旅逾越节晚餐在我表弟的房子。然后,我在12天后有一个剖腹产,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冲到他的父母家过圣诞节。我抱怨去。
但它不仅是节假日时,我渴望了解。我感到一阵剧痛,当我们在我最好的朋友家烧烤,和她的丈夫随便用在对话中的单词“schvitzing”,这是一件好事道格绝不会那样做。
2000年4月,一切都改变了。我们都在度假从家里3000英里时,道格曾在酒店浴室癫痫发作。不到一个小时后,他被诊断出患有在圣迭戈斯克里普斯医院胶质母细胞瘤。医生问他是否想为最后的仪式祭司。他说他喜欢一个拉比。
“毕竟这一次,它是什么样的我已经习惯了,”他说。“拉比会得到我。他会理解我们,”他说,他们推了他关闭了他的第一次开颅手术。
所有通过他的病情,我们不断地迎接着我们的拉比在家里谈论未来。我们的谈话中包括了关于他渴望被埋葬在犹太人墓地,这让我吃惊极大的讨论。
我担心这是脑瘤说话。“你确定吗?”我问他(过去式。
“这将是更容易,”他说。“对你来说,孩子们 - 和你最终的任何人了。”
这是一个男人谁愿意一直在沉默seders并呼吁鱼丸“热狗的犹太版本。”现在,他显然想我嫁给一个犹太男子,当他离开了人世。他球探几个潜在的犹太丈夫,其中一个邻居和他谁是要离婚的同事。
有人谁不是天生的犹太人,他真的成为一个门施 - 和有点的shadchan(媒人),太。
重新进入约会的世界是不容易的,当刚刚丧妻的约会应该是一个受保护的类。
有我会见了JDate谁做一个体面的道格印象,说的家伙,“我是犹太人至少犹太人你永远满足。”再有就是罗德里格兹爱好者,从有人在我孩子的学校希伯来语,谁想到了标志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是个厨师修复起来。
道格不知道的人,我最终相识结婚。哈尔和我用我最好的朋友,希拉里和哈尔的妹妹贝丝搞掂 - 我们早已经在一起17年。他在一个犹太家庭提出并继续保持犹太大学,并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他已故的妻子曾在哈达萨活跃。
“谢谢你做我的儿子繁重,”我能想象道格说哈尔。“而制作利西太高兴了。”
最终,道,事实上,埋在犹太公墓。在一点头,以他的遗产,他在圣约亚伯拉罕纪念公园的斯宾诺莎部分。(OK,斯宾诺莎竟是一家荷兰人与塞法迪Portugeuse遗产,但他至少名字听起来意大利)。
道格是不是在这里举杯当我们的大儿子上了医学院,或当我们的小儿子参加了数据工程工作。但他理解为人父母的工作,他开始对我来说可能更容易与谁分享我的信仰的人。
他的慷慨共鸣,尤其是在的时候,那么多的年轻父母与拼杀流感大流行的现实和动荡对在街头种族主义。如果我生病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能够给他这样的礼物,我为它深深感激。
这篇文章成为可能的慷慨支助的ios下载beplay纽约UJA-联合会。对于与犹太教和生活护理,就是死亡,悲哀结束额外的资源,点击这里。
头图像设计由Grace Yagel;原始插图者:Maria Voronovich / Getty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