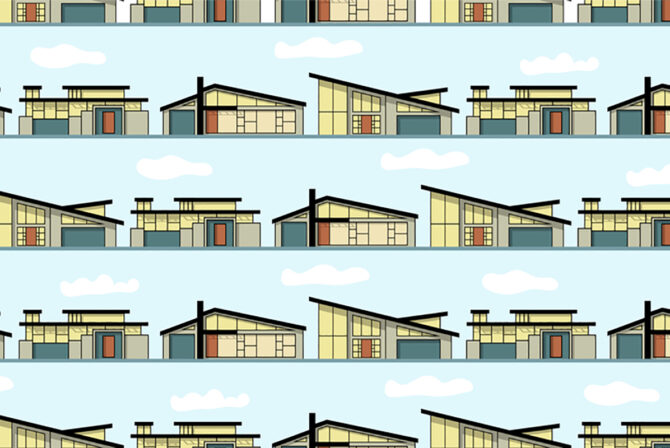我们差不多8岁是一个狂热的读者。即使在流感大流行来袭,拉维会熬夜在床上一摞书。什么时候纽约时报周末版到达我们的大门,不过,她很快就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事实: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
死亡肯定已经在我们的家,在过去但讨论冠状病毒,我们正在解决它一个更经常的基础上 - 尤其是当拉维读的头条新闻,我们有机会了。
幸运的是,拉维的妈妈是社会工作者,谁不怕死的主题。对我来说,一个法师,我有刚对此事自己的一些想法。
“是你,当你死了,你是为你的余生去了?”拉维问。
“没有人知道,”我的妻子,耶尔,回答。
“没有人知道,”我附和。“人们有很多关于它的不同意见或信仰,但妈妈的权利,没有人确切知道。”
一阵沉默。
我要在这里说实话:我觉得有一定的兴奋,每当拉维带来了死亡。这是因为如果在机场停机坪安全闪光灯都闪耀着:成长的孩子,准备成人的谈话,对这种方式!
作为一个孙子大屠杀幸存者我觉得关于死亡和牛汽车每次我坐拥挤的地铁时间。逾越节期间,当拉维唱“是什么让”意第绪语- 一个家庭的传统 - 我记得我父亲教我意第绪语歌曲大屠杀作为一个孩子。怎么样,但是,我平衡需要向我的女儿在响应的敏感情绪,而这样坚守和履行死亡在我们的生活中阴暗的角色?
在这些Covid 19日,拉维往往带来了死亡左右就寝时间。
“我并不想死,”她对这样一个晚上说。
“是什么让你想到了吗?”耶尔问。
“Nuni告诉我,她的哥哥淹死了,当他还是个孩子。”Nuni,我们的老保姆,就是我们为一个短暂的时期录用。
耶尔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不知道可以通过这个特殊的保姆已经沉淀这样一个共享的消息。“是的,这是一个悲剧,”耶尔说。“你知道这个词。和悲剧发生,但他们是不同寻常的。”
“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我补充道。“像我们如何停止警报器,当我们在外面给希望大家确定。就像我们如何度过每天晚上两分钟就跑到窗口大喊“谢谢”在我们的肺部上方以谁作为工作的无数人医生和护士和风险自己的安全和对我们的关心。”
“我还在惊死亡,”拉维说。
“你知道我是谁与谁97个岁参观的夫人?”我问拉维。“她有同样的恐惧你。”
又是一阵沉默。
它可以是不舒服谈论死亡,甚至在成年人中,这同样啃,在我们7岁的惧怕吃和97岁的女人,我很荣幸地参观。原来生活可以保持那个神秘随时间这么长时间让我充满了敬畏。这也提醒了我,回答生活中最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无论他们是否正在被寻址到幼儿或老人的成年。
我的一个朋友已经与他的女儿,谁最近告诉他,类似的对话:“当你和妈妈死了,我想住在一起我的表兄弟“。
我的朋友问我:“我相应地调整我的意愿?”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发现自己说这些日子更比我想象的短语。双方之间的流量是恒定的,甚至在这段时间的流行病放大。就在前几天,我参加了侄女的生日派对,随后葬礼一个朋友的奶奶,然后是婚礼 -所有通过放大。而且因为我参加这些活动在家里,拉维一直围绕,听力和窃听更加专心,见证了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我希望我的回答对我女儿的问题。我希望我有任何的回答,真的,至于什么时候该病毒会结束时,她就可以拥抱她的祖父母再次,人们为什么生病,为什么人们恨和斗争,英年早逝。我不。我希望我可以从痛苦的生命保护她,但我不能。我慰藉知道这些问题的人,我必须问我的父母,我的父母要求他们的祖父母,依此类推,从代代相传。我感到欣慰知道我养了她在该值高于任何答案,我会尽力提供她问话的传统。
这篇文章成为可能的慷慨支助的ios下载beplay纽约UJA-联合会。对于与犹太教和生活护理,就是死亡,悲哀结束额外的资源,点击这里。
插图由最好的内容制作集团/盖蒂图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