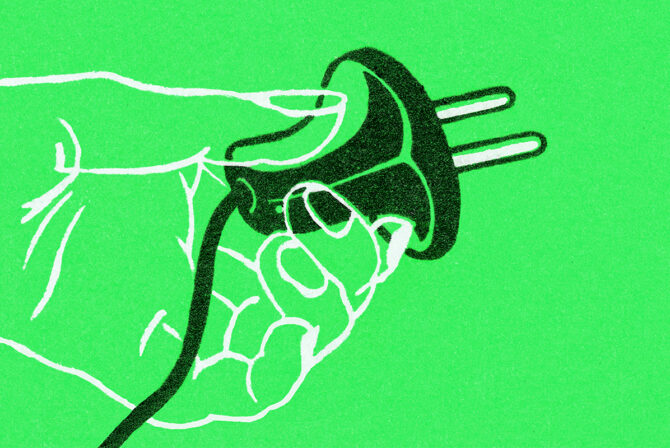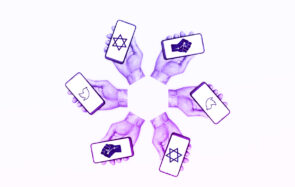2016年,我写了a张贴Kveller苹果beplay并解释说,虽然我从来没有担心校园枪击事件,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怎么统计不可能,我担心我的孩子们的混血儿被警察开枪每一步,他们在屋外时间。
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谋杀我的唤醒,再一次,共享一块Facebook和苹果beplay推特。抵制来得又快又猛烈。
争论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
我的丈夫教我们的儿子如何显得不具威胁性。小声点。永远不会运行。如果警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你不问问题。你不必质疑他们的命令的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从口袋里掏出你的宪法。
我收到的一些负面评论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怎么敢玷污我们身穿蓝色制服的勇士?”我也收到了对应的一句:“这是。行为每个孩子都应该受到教育。# AllLivesMatter。”
但真正的刻薄来自两部分:
1.通过写以上,一些读者声称我指责受害者。我在暗示,如果所有的黑人男子被教导要立即出现威胁性,并按照警方的法令,他们就不会结束了一个膝盖到他们的脖子。
这让我很吃惊。我很确定我没那么说。这些年来,我在我的文章中试图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写“我”相信什么和做什么,而不是“你”应该相信什么和做什么。(事实上,在帖子上搜索一下,“你”这个词只有在我谈论我丈夫或我给孩子们的指示时才会起作用,而不是作为对别人的指示。)
然后……
2.通过抚养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丈夫和我应该为现在发生在我们大街上的骚乱负责。
If we’d empowered our children to fight back, my critics charge, if we’d instructed them to call out police brutality, if we didn’t tell them that cops should always be obeyed, then police officers would not feel entitled to beat whomever they wanted, whenever they wanted. Apparently, my husband and I are terrible parents and role models — not just for our own children, but for all Black and Brown children everywhere. (Now insert a couple of four-letter words and slurs, and you’ll have pretty much the gist of the feedback I received last week.)
但这里的东西:我出生在前苏联和我的父母教我几乎同样的事情有关处理机关。此前在70年代末移民到美国,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拥有权力可以做任何他们想要那些没有,并保持安全的最好办法是保持你的头了。不要搞,肯定从来没有招惹,保持了他们的雷达和你也许会避免前往西伯利亚。
还有一件事:因为我不是在美国长大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不是在美国长大的黑人男性,所以我让我的丈夫在这个话题上带头教我们的孩子。事实上,我们的成长经历也很相似,这使得我很容易就能听从他的命令。
需要澄清的是,我丈夫和我不同意在相当多的东西 - 一个罩是否是一顶帽子,例如,或者如果孩子在使用时需做的工作,我们会以其他方式需要雇用别人做 - 经常大声地,并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最近,当我们16岁的孩子中间试图更全面地了解目前的情况,我告诉他抬头看1965年瓦茨暴动当交通堵塞升级为财产破坏和暴力时。
我丈夫反驳说瓦茨暴动(以及随后的事件)布朗克斯区的抢劫纽约市期间停电他说,一个更好的类比是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是白人领导了暴力事件。几个月前,那个孩子问我是否同意他父亲告诉他的一件事,我承认不同意。但我也强调,我不是在美国长大的黑人,所以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争论。他感受到了他所经历的生活所带来的感受。
I don’t always agree with what my husband says, but this is a case where my husband has life experiences that I don’t — one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our children face, and will continue to face, in their lives as African-American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 am going to yield to his life experiences.
我会听从我选择结婚并生孩子的男人——而不是在网络上完全陌生的人的惩罚和虐待。(我想我这样有点好笑吧?)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的丈夫和许多人一样,一直怒气冲冲。我们的大儿子今年20岁,他很不安,已经关掉了社交媒体!我们16岁的孩子试着用逻辑来推理,问一个又一个问题,在房间里呆上几个小时,然后突然蹦出来,接着又问一个问题。我们最小的孩子害怕七年级的课堂讨论,她将被要求为美国所有黑人说话。她的学校已经安排了一个关于这次骚乱的会议;她知道她会被期待分享,所以她真的是提前准备她的发言。她的大哥正在帮助她。他知道处于她的位置是什么感觉。
当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女儿进来了。她看着书的暂定标题——“我的家人是如何谈论乔治·弗洛伊德谋杀案的”——然后说,“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个。”
我困惑地看着她。“你是什么意思?”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讨论这个问题。”
“哦,”她说,“但我们总是在谈论这些问题。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她是对的。遗憾的是,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总是在谈论种族、贫穷、反犹太主义、警察越权、教育不平等、监狱人满为患、预期寿命不同,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Covid-19疫情严重,少数族裔社区最难的。这非常有意义,她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切换到谈论乔治·弗洛伊德,因为讨论的一般男高音留大同小异,因为它是这个特殊的事件发生之前,这个特殊的反应,这种特殊的总裁。没有什么新在这里讨论......然而,我们保持反正讨论它。
我们正在做它完美?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会在这条路上的错误?我敢肯定这一点。(As my mother helpfully says, “Don’t worry, any choices you make for your children, you’ll be wrong.”) But will my husband and I ultimately do what we think is best for our children based on our life experiences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m? I think so.
我将遵循在这个问题上我丈夫的领先优势,就像他跟随我的别人。我们会把它一个一天的时间,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教导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以上的叙述任何情况。最终,如果我们做我们的工作权,这将是由他们通过所有的噪音进行排序,并决定他们相信,他们想怎么过自己的生活,不管可能会认为在互联网上什么批评。
图像由Hiob / Getty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