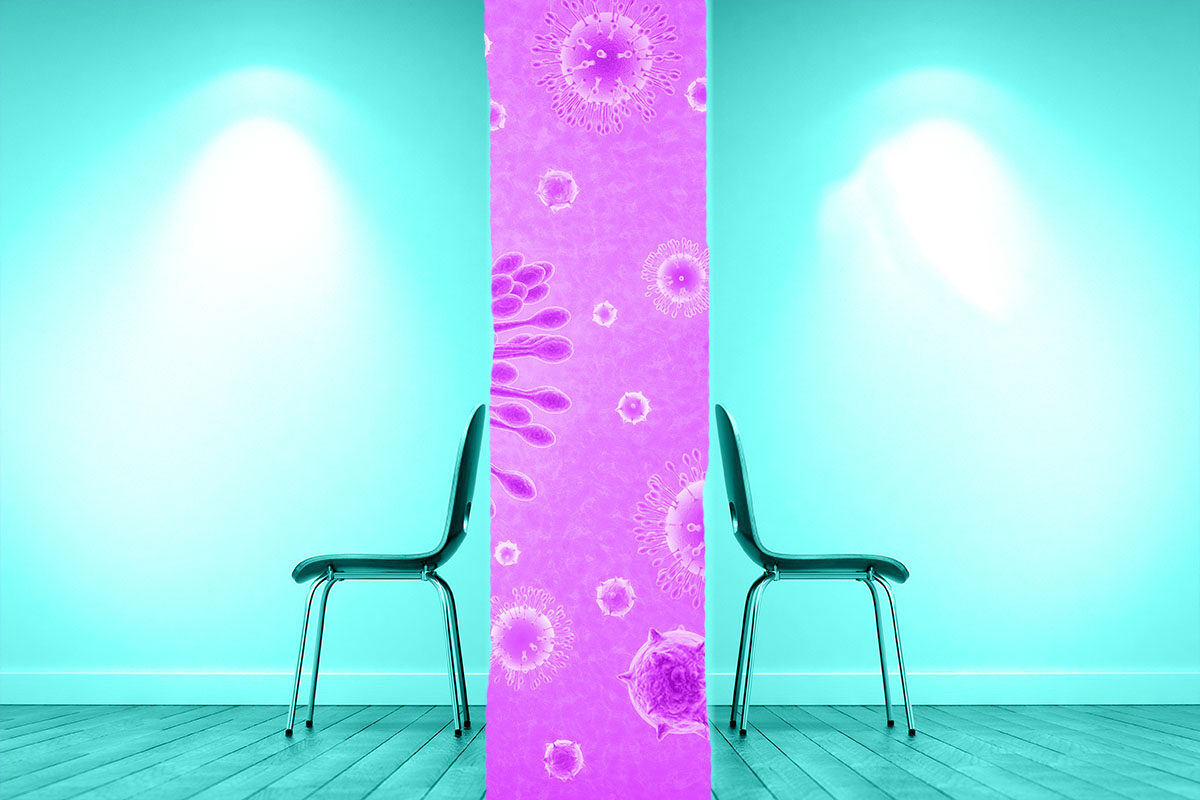我不是一个等待换一个大流行对前来敲门-AT-我的门还挺加仑,所以我把COVID-19非常认真,只要它开始蔓延整个美国,我开始在家工作大约一个月前,我的办公室前正式关闭。我是一个单身母亲,和我保持我的三个孩子,从学校15岁,13和9,回家之前,他们的私人学校关闭。我跑到好市多(Costco),囤积了食品和物资。我在网上买了哑铃,即使健身房还开着,我也不再去了。我有一个Instacart账号,这样我就不用出去购物了。我买了棋盘游戏,书,美术用品,跳绳,还有粉笔。
我住在佛罗里达- 其中有些人可能认为一个地方已经出现了社会崩溃 - 所以在担心病毒的顶部,我现在需要担心众所周知的“佛罗里达人”怎么会到经济崩溃反应。我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和我的孩子,如果必要的服务遭到破坏时,又饿,作业少的人开始在街头骚乱?在我的前军事私人教练的建议(谁一直在等待几乎太兴高采烈地为这种情况),我买了一台太阳能收音机,路线图,罐头食品,干货,丙烷气,急救试剂盒,额外的洗浴用品,净水片,种子,电池,气体罐和熊喷雾(作为替代的枪)。
我觉得你得到它的要点是:我正准备。有一件事我毫无准备,虽然是如何前夫将在流感大流行作出反应。他和我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他采用响应更悠闲,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过去的几周里,他谈到了生活的优先经济,如何自我隔离会对心理造成伤害,媒体如何散播恐惧,个人风险如何没有那么大,他如何谨慎(他经常洗手),但并不太担心。
我站在堆满存货、塞满东西的房子里,惊慌失措。我胃里越来越深的恐惧现在又产生了新的担忧:我前任的行为将如何影响我和我的孩子。正常情况下,我和他的工作关系很好,但到目前为止,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压力的全球大流行。我们看不到眼睛对眼睛上的很多事情 - 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离婚 - 但我们都努力合母相对于并为尊重对方的意见。
所以,我给了认真考虑他的观点。虽然我坚决不同意他,他也有一些正确的观点,谁在说我偏激,末日式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想到了我们给孩子们上的固有课程。我的方法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社会责任,什么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他的方法教会了他们独立思考,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能够在不自我孤立的情况下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以及生活的价值。
当学校正式关掉,我们同意保持我们的65/35分时,但要我们如何当年分手了更加灵活。然而,因为很明显,我的前没有服用这种病毒一样认真,因为我是,我试图让我的孩子跟我,只要有可能,希望在佛罗里达州政府将赶上并实行更严格的限制。但逾越节很快就到了,该他带他们去度假了。当我们在电话里讨论这个的时候,我发现他打算在其他家庭在逾越节家宴,他的邻居小孩还在外面玩在一起,人们在密切接触仍然去上班,甚至与新的政府限制和希伯莱语的建议,他仍然认为媒体吹出来的比例。
我不知如何是好。他居住的地区是全州第二高的病例。他已经暴露了吗?难道我让孩子们跟我或发送给他吗?难道我的安全问题给我的孩子和我自己取代父亲的权利与他们相处?是风险,我的健康,我的儿童健康以及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任何人的健康真的那么好吗?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的孩子如果不能和父亲在一起,他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吗?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流行病,我是否应该对我的前男友的行为和他所做的选择有发言权,而我们至今所采取的方法都是“各自为战”?
我很担心,通过保持我们的孩子,我会打开的问题了潘多拉的盒子。我怎么会觉得如果我的前夫,是谁比我更虔诚,也不会送孩子给我,除非我同意更严格地遵守犹太律法?作为一名治疗师和教练谁在离婚和养育子女,谁推动和平共同抚养的议程,这会不会影响我的职业生涯?我自己的心理健康(和银行帐户)才可以生存,没有喘息不停养育?最后,这是值得我们之间的潜在后果,解开多年积极建立关系,并摧毁友好共同抚养的未来?
我纠集每个内部资源治疗我,并开始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准备与我的前谈判。当与他说话,我一直平静,用“我”的声明,表达了我个人的恐惧和担心,在我的“疯狂”的方式与他甚至笑了,但求他讨好奉迎它。我寻找客观事实,并质疑我的自我在这里起了多大作用。我求助于我所能想到的每一种外部资源来帮助我提供观点、思路和建议,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家人、拉比(犹太教教士)、一名政府官员和我的儿科医生,以获得他们的正式建议。
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请他检查一下我的权利,并了解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因为他的计划是破坏避难所的秩序,我在我的隐瞒合法权益,我被告知我的健康和我的孩子的健康优先考虑。而我依然在犹豫。所以,我坐了下来,在那里我问他要遵守某些准则(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并以书面形式同意他们组成的电子邮件。他可以有孩子,我说,我只是需要一些保证。
但为时已晚。他觉得我侵犯了他为人父母的权利,干涉了他的私生活,提出了我无权提出的要求。他担心我疏忽的宗教仪式会妨碍我给孩子们一个适当的,犹太人的逾越节体验。我们陷入僵局,同意引进一位调解人。
应力是压倒性的。我回想到我的困难和情绪排水离婚。我的孩子们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们不打算自己父亲的,我被撕成多少信息,与他们分享。我告诉他们,新政府实行留在家里为了给我们留下了不知道如何与分时进行。他们没有买它。
因此,我向他们解释说,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时代,没有人是真的相信,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他们的爸爸和我有不同的意见,即有不同意见是正常,而不是战斗,我们让一个不带偏见,第三方做出决定。我的孩子哭了,说他们错过了他们的父亲。我哭了,太,并告诉他们,我希望事情会有所不同。我想过recanting,但永远存在的坑在我的肚子提醒我,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候,那里的东西都大幅一天,那里的生活和死亡的问题就行了改变的日子,我怎么可以把我的孩子给别人谁也不会拿我的敏感,意见和母性本能考虑吗?在通过一个微小的,强大的病毒一蹶不振的世界里,是不是会好一些简单宁可谨慎的一面呢?
我们都向调解员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最后,他认为最安全的决定是让孩子们和我呆在一起。值得赞扬的是,我的前男友优雅地接受了这个决定,我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告诉我,他们会尽最大努力。
到那个时刻共同抚养一般来说,我认为父母双方都没有比对方更多的权利。但当安全成为一个问题时,这种信念就会受到挑战。我不是单方面做出这个决定的。我让专家参与进来,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调解人。我不知道这会有什么长期的影响,但是现在,我每天都在工作。我会给我的孩子更多的爱,我会向我的前任伸出橄榄枝,我会处理我对每个人不公平的挫折,最重要的是,我会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
图像由skegbydave / Getty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