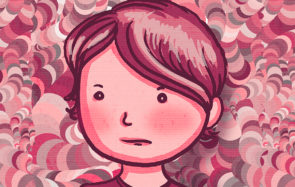Taffy Brodesser Akner习惯于做面试官,不是被采访者。
“我已经习惯于私下用语言来构建自己,”她告诉科维尔。苹果beplay“突然说话,为了让它出现在某个地方,我还没习惯呢。”
“我一直很同情我写的那些人;她补充说:“我一直认为写这篇文章一定很糟糕。”“但现在我真的知道了:你没有力量。”
你可能从她的名人档案中了解到Brodesser Akner纽约时报-的格温妮丝·帕特洛,请坦娅·哈定,请布拉德利·库珀,请更重要的是,现在你可以阅读她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的精彩作品,带着她那本破小说,弗莱斯曼有麻烦了.
这是托比·弗莱士曼的故事,谁-你猜对了!-在他妻子之后有麻烦,瑞秋,他们分开几个月后就消失了。这是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故事,离婚,做母亲,还有更多。托比和瑞秋都没说过-叙述者是一个叫利比的女人,他在以色列大学期间和托比在一起。我不会破坏任何其他东西;你应该真的,真正地,你自己读。
我有机会和Brodesser Akner聊聊写作弗莱斯曼有麻烦了,请对她的第一本书的反应,为什么她决定把这个故事建立在一个她非常了解的世界里。
你为什么选择从第三个角度讲述托比和瑞秋的婚姻?
我就是这样知道怎么写的。这就是我做新闻工作的方式。我总是觉得你应该知道从哪里来的观点;然后,有一天,我开始用我新闻界的第一个人说我所看到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局面,它迫使你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测试者,像我一样,害怕占用太多空间。
所以在小说中,一开始,利比只是第三人称。我朋友马克对我说,“当你写的不是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这是部小说,我一定很喜欢!他说,“有没有人会告诉你的文学英雄:你现在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写作,因为你正在写一部小说。”一旦他这样说,我开始认为[这本小说]和我的新闻一样,它解放了一切。
当你写作的时候,你是如何向人们描述这个项目的?
我在写一本关于一个男人离婚的小说。
你觉得这就是结局吗?
我想是的。我[仍然]不知道如何描述它!你知道怎么做吗?你能帮我描述一下吗?我说的另一件事是:这是我新闻业的一个横向转变。这是一个男人的故事,这正是我写的-我曾经所有这些年GQ公司.我最后讲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这就是感觉。
我可以想象瑞秋的故事情节她经历的创伤性出生,她在工作和做母亲之间的斗争,会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苹果beplay作为一个母亲,你和那些感觉有关吗?你有没有借鉴经验?这是个蹩脚的问题,我道歉。
不,这不是一个蹩脚的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你问作者如何认同某些人物时,他们会生气。因为作为一名记者,正确的,我觉得,你想让我问什么?你认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但是现在,我尤其不耐烦,因为你当然应该问我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但答案是,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让他们如此困扰:经验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太复杂了,解释不好。
我能说的就是:每个想法都是我的。我很遗憾地说在出生前后,这是我第一个孩子的经历。
当你出版一本书时,你必须读上千遍。正如你从写作中所知道的,到你第三次读的时候,你就像,哦,这是一个完整的狗屎。不管以后人们会多么喜欢它,这对你来说总是一团糟。出生的东西——即使是在我最后一次读到的时候——每次读到它我都会哭。好像我没写过。好像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闻。我想这就是创伤的本质。
它永远不会变得容易。
不,我希望是这样。
你对什么有反应?弗莱斯曼有麻烦了像你一样?
一开始,你知道的,我已经习惯了。我习惯了很多人阅读[我的]东西并做出反应。一开始我总是很紧张。
华盛顿邮报回顾差点在床上杀了我,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样的评论。所以我不能抱怨。但我可以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情绪化的,我只是在我的婚礼之前。我猜我孩子的出生,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站在媒体的另一边,你希望人们在这些采访中问你什么?
我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在问我。就像,这和新闻业有什么不同。我喜欢讲故事。观察别人告诉我这本书的有趣之处是很有趣的。尤其是当人们问起做母亲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询问出生的人。
不可能。
那不是疯了吗?很容易找到。甚至在我的网站上,我写过它[而且它]是我职业生涯的开端…我从中被搞得一团糟。没人问我这件事。
我们是犹太人的育儿场所,所以我得问问这一切的犹太性…
用意第绪语提问!
犹太人觉得自己深深地嵌入了人物中。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放在犹太人的纽约/新泽西州对你很重要?
这正是我所知道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写你知道的东西”的真实情况我是一个专一的狂热者;我非常反对让这么多人理解它。这是我的写作经验:你越具体,即使特定性不适用于他们,更多的人可以在故事中看到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真的。
甚至到了标题——我担心会排除很多人。最终,不说这是虚假广告这就是它.这是一本关于纽约一个犹太人的书。我喜欢不解释什么是星期五晚上的晚餐的想法——只吃星期五晚上的晚餐。我喜欢每个人都只去学校,在那里他们会遇到像他们一样的犹太人。犹太教周围还有这么大的文化,我很舒服。
在你的格鲁布街轮廓,请你写的,“我在抚养犹太孩子,我越来越担心,除非有某种仪式,否则我不能抚养他们犹太人。”你能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阐述吗?
我们有这些犹太理想,我和我丈夫在各种各样的练习上来回奔波。他改变主意了一开始他真的很喜欢。然后他变得非常不安得到情况和阿古诺.我们近距离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案件,他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参与任何一种正统的教义,而这种正统的教义仍然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因为他真的爱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都爱。但我们搬家了,如果我们不以正统的方式练习,我们的生活中会有多少仪式我们一直在挣扎。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没有实际行动,一切都是理论。我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自由主义者,但如果我不在某个地方自愿让我的孩子们真正看到,我没有传递这个值。我只是说说而已。孩子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不再听别人说话了。
但是我的孩子们知道周五晚上和周六没有屏幕。我的孩子们知道在那些时候我们总是在一起。我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拜访朋友,扎克一家,在洛杉矶的比萨。他们需要看到的就是这些。这就是工作。你不能就这么说。有时在周五晚上,我只想和孩子们一起看电影。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我从来都不想做。因为一旦我们失去了仪式的神圣,它不见了。
埃里克·坦纳头像中的塔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