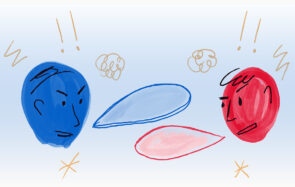回到2017年8月,我看到了Unite the Right集会的片段夏洛茨维尔。我看到纳粹旗帜自豪地飘扬在街道上,我听到充满仇恨的口号,比如“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
然而,在我的脑海里,我所能看到的是一个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波兰小男孩,他出生在战争快结束时的一个战场上,他的母亲从集中营里逃了出来。
最近,当我听到我们的总统不能谴责的成员骄傲的男孩——否认大屠杀的加文·麦克因斯创立的极右翼仇恨组织——我看到了那个小男孩,他永远不会知道和祖父母、叔叔、婶婶一起长大是什么样子。
我非常了解这个孤独的波兰小男孩,他在一个拥挤的流离失所者营地呆了四年。总有一天他会长大成为我的丈夫。
他和我的姻亲是大屠杀幸存者他们见证了难以形容的恐怖。他的大家庭成员是被纳粹屠杀的数百万手无寸铁的无辜犹太人中的一员。而现在,正是这些纳粹分子激发了安惊人的增长充满仇恨的美国人,反过来,他们提供了自己的胜利万岁”“在美国小镇的街道上。
就是这个小男孩,赫谢尔,最终成为美国公民和曼哈顿的公设辩护律师。他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社会正义,他的整个职业生涯——40多年来——都是穷人的倡导者和代表。
而现在,75岁的他面临着认知能力的衰退,他不得不悲伤地目睹自己的总统在纳粹火炬点燃仪式上谈论“好人”,并描述“好人”良好的基因,怪异地唤起了希特勒的优生学理论。他的生活现在被有组织的仇恨所终结,这让我感到无法忍受。
在某些方面,过去总是存在于这个生活在这个男人内心的小男孩身上。由于感情创伤太深,永远无法愈合,赫什的心灵就像一座堡垒,用来封锁那些痛苦而难以记住的记忆。几十年来,这些墙是无法穿透的——他的过去深深埋在里面。但现在,当我们看到仇恨和反犹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裂缝开始出现。
我观察着赫谢尔,就像他观察着我们国家被释放出来的东西一样,我也看到了这个小男孩再一次面对着仇恨这个有害的象征。创伤被埋藏已久的东西被搅动起来。我看到他脸上痛苦和恐惧的表情,但他说不出来。看着他听到我们的总统放大了仇恨者的声音,而他自己的声音却越来越小,这令人心碎。
赫什曾经活力四射,体格健壮,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纽约时报周日用墨水做的填字游戏。如今,他正在苦苦挣扎。两年前,一种未确诊的认知障碍导致了我们财务的崩溃。不幸的是,今年1月,事情正处于风口浪尖大流行的我们在长岛美丽的家失去了抵押品赎回权——我把这个地方创造成一个绿洲,这样他的家就不会再被夺走。
然后是冠状病毒。随着我们的国家在陌生环境中解体,我的私人生活也反映出了混乱和不确定性。当避难所本身不稳定时,要就地避难是很困难的。当我家里的另一个人已经遁入他自己的世界,在情感上不再存在时,社交距离就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强加的孤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孤独。
赫什一边看着新闻里的疯疯癫癫,一边在餐桌上用笔记本电脑无休止地看电影,日复一日,直到深夜。他过去喜欢动作冒险片、浪漫喜剧和间谍惊悚片,尤其是那些改编自约翰·勒卡雷小说的电影贪婪地阅读。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电影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他的观看选择非常具体:几乎都是大屠杀主题的电影。他研究了数百部关于纳粹德国的鲜为人知的电影大屠杀以及战后犹太人的困境。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从前有一个人,他拒绝看辛德勒的名单因为它离骨头太近了现在,在他一心一意的追求中,尤其是在他已经穷尽了亚马逊上的各种选择之后和Netflix,他梳理了我县图书馆系统庞大的网上资源,储备了几十部外国电影的dvd。
一个经常重播的电影是无视,丹尼尔•克雷格。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二战期间犹太人的反抗,很少被讲述。1941年,当犹太波兰人在乡下被围捕并被杀害时,一群犹太兄弟领导了一个阻力他们逃进了白俄罗斯茂密的森林,在那里他们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分子多年。
当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向我解释说,他所有选择的共同主题都是“在逆境中生存”。“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仇恨、恐惧和弹性是赫什仍然能理解的东西,即使他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它们。这些天,他想要记住,即使只是在内心层面上。
他说的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人们熟悉得可怕的共鸣:我要活下去,克服一切困难是他母亲30多年前送给我的唯一一本书的书名。她无法说出自己的大屠杀经历,但我想她希望别人能说出自己的经历——就像电影为赫谢尔所做的那样。
的崛起反犹主义也让难以想象的事情爬进了我的脑海。我想相信“再也不会”是事实。在我的美国,这种仇恨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它确实存在。现在,我也发现自己被这些吸引着我丈夫的电影所吸引。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在恶化,但现在赫什和我通过他策划的电影联系在一起。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在观看这些电影时,赫什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突然之间,以普通家庭生活为背景的1930年代东欧战前城镇变得活跃起来。他表现出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渴望,轻声说道:“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家人。”
我比赫什小10岁,我的童年生活在郊区,充满家庭气氛,和他的童年总是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我们一起看这些电影,的故事那永远存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在一台平板电视上表现得一清二楚。我躺在他身边,通过他的眼睛看到创伤,就像我在拍电影一样仔细地观察他。他允许我进入,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我知道他永远无法表达他的感受,对我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深深的悲哀。但即使他在感情上离我越来越远,这一意想不到的活动也让我们的亲密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不记得的,我会永远记得。当我看到他沉迷于电影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75岁的老人了。我觉得损失不大波兰的男孩她静静地坐在我们的餐桌前,看着让人感觉太现在时的过去。
我一直知道赫什和他的父母是历经千辛万苦而幸存下来的。也许这些电影是在提醒他,“幸存者”仍然活在他心中。我相信这给了他力量和希望。它对我有帮助,即使我独自面对未知。
在个人斗争和政治动荡中,“幸存者”这个词是授权。尽管困难重重——摇摇欲坠的民主制度、天翻地覆的熟悉生活以及致命的流行病——我们仍将生存下来。
标题图像由DAVIDS48/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