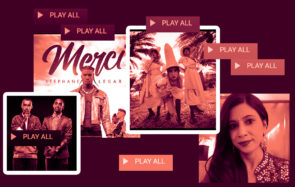我母亲于2002年5月死于胶质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几乎总是致命的脑癌。参议员麦凯恩现在正在战斗。
在母亲诊断到死亡的短短几个月里,她的病夺走了她成为人的一切——首先,她的锐利,然后她的同情心,然后是她的逻辑。然后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她死前几周,我的母亲——一位长期受人爱戴的大学管理者——完全停止了讲话。
被诊断为癌症将被推进到“战斗”的花言巧语中,但我见过的那些接受治疗的人可能会把战斗描述为对痛苦的默许,使人虚弱,有时不太可能“治愈”。我母亲没有与这种讽刺作斗争,因为一旦她被诊断出来,她没有能力了解自己的病情。这是她思考的几次中的一次,她告诉我们她头上有意大利面,医生要把它切除。
当她的头发开始从化疗中脱落时,我真的帮她剪了下来,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金发女郎,没有一套完整的卷发器就不会旅行,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带她去订购了一个我们永远也拿不到的假发。之后,我们吃比萨饼;她狼吞虎咽。当我试图让她离开时,她反复告诉我她要走了,但从未移动过她的身体。我不得不把她抬起来,让她的脚开始动起来。
我们是,作为一个家庭,无法接受她的诊断。在我母亲去世的那天,她在医院接受姑息治疗以治疗她的症状。我经常去那里,不要说再见。但当我到达的时候,一个护士看着我,摇摇头说,“我做这个已经很久了;就是这样。”
我很震惊,毫无准备的你能做好准备吗?我不知道。我们相信这场战斗的言辞,并希望能有所缓解。
我妈妈去世时我27岁,我几乎从未提起过她的死。从那以后认识我的朋友们有时会说,好像我根本没有母亲似的;就像我从机器人子宫里出来一样。但我的沉默不是漠视;恰恰相反。妈妈的死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我也许是最难的。
她的公众形象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之间的二分法是我选择沉默的原因之一。我母亲深受爱戴。在她的葬礼上,人们谈到她的温暖,她不知疲倦的同情心和不屈不挠的乐观态度,讲述了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我们的关系不一样。除了在诊断前几个月,当我妈妈放开我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但这是她生病的第一阶段。她的敏锐度下降,再加上她长期以来对我施加的压力逐渐减小,使我在任何特定的日子里都能以任意的方式获得成功:约会,职业生涯,服装选择。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可以畅所欲言,而不需要掩饰为关心和建议的许多判断。
光明节期间我去看望我的父母,妈妈没有和我争论我打算怎么去他们家,或者在什么时候,或者我会呆多久。我们吃了晚饭,还嘲笑星期四晚上的电视节目。当她提到我单身的时候,正如她不可避免的那样,我提醒她,她比我更关心这件事。在没有收到负面反应后,我鼓起勇气,也告诉她这不再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而且,就这样,她同意了。我想也许我最终说服了她让我找出自己的路。我母亲在56岁时患上早期癌症,我要让她得到解脱,照相底片,木刻我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于癌症,这是我一直想要的母亲。然后她死了。
摆脱那些不断的人,不知疲倦地试图主宰你是在不断的自责中挣扎,痛苦与欢乐。
生命中有死亡;一个人的生活常常是由他的死亡方式来定义的。灰色的记忆,失败的身体,而不是生活得很好,和我们呆在一起。但我该选择哪位母亲呢?如释重负的母亲,他很友善,很支持我,ios下载beplay或者和我一起长大的母亲,我崇拜的母亲,我崇拜的母亲,但我和谁有着令人担忧的关系?还有一个母亲病得太厉害了——是的,从她的头脑中-去了解区别。
 此日志是支持的系列的一部分ios下载beplayMJHS卫生系统和纽约UJA联合会到
此日志是支持的系列的一部分ios下载beplayMJHS卫生系统和纽约UJA联合会到
在犹太背景下提高对生命终结关怀的认识并促进对话。
进一步了解临终关怀的作用及其对患者和家庭的价值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