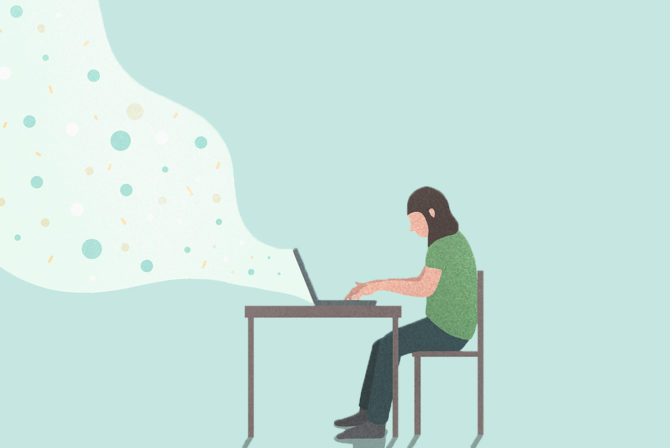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这辈子第一次我祈祷。
不久前,我女儿的玩伴,梅丽莎,她的手卡在游泳池的滤栅里了。她在水下呆了10分钟。急救人员几乎放弃了救她,但有人坚持要继续尝试——“她8岁,我们继续前进!”-他们拉着她,奇迹般地,只为了生活的这一面。
梅丽莎的悲剧属于她的家人,但它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社区。“除了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想。但我们也想到了梅丽莎是如何属于我们的,同样,就像大象的幼崽属于牛群一样。当她依靠生命维持的时候,ios下载beplay医生在测试大脑活动的任何闪烁,我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任何东西.“请为我们祈祷,”她的父母问。所以我祈祷。很难。
我不信教,但我常常羡慕有信仰的人。相信有秩序的宇宙,一切都是为了某个目的发生的,会让生活更轻松。也许我们对信仰的偏好DNA,但我从未能表达出那个特定的基因。
我想这并不奇怪,考虑到我成长的精神环境。我母亲听到以色列发生爆炸的任何消息都悲伤地喘着粗气,当一个犹太人被指控犯罪时,她也恰当地“Oy veyed”,但她不能告诉你安息日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她点燃的蜡烛在周五晚上,安排了20分钟的逾越节晚餐,在这期间,我爸爸翻了个白眼。妈妈带我们去高级假日服务,如果不是站起来坐下来,我会睡着的。精神上的交谈从来没有伴随这些努力;在我家里,“上帝愿意”和“上帝禁止”这两个短语涵盖了我们关于更高的存在的全部论述。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站着,九个脚趾在亵渎神明,只有我的右小脚趾向神圣的边缘。我工作过,旅行,骑我的自行车,试着和蔼可亲。我和朋友谈了很久政治,书,梦想未来,但不是关于宗教或上帝.偶尔,当精神超越把我从平凡中惊醒时的孤独时刻。曾经,在罗马,当我站在一根巨大的柱子的底部时。彼得广场,我看着下面的人群聚集在我面前,等待教皇复活节的演讲。开始下雨了,突然,在我的脚下,有一万把雨伞在跳动,异域色彩的海洋。或者当我骑着双联自行车下坡时,当我们接近每小时60英里时,看到人行道上的线闪过,与其说体验速度,不如说体验速度相配的速度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我从没有能够夺回。像这样的时刻偶尔会出现,就像心电图上的小光点,有了long,平的在中间伸展。卓越的,对,但不是与上帝交流。
后来我成了父母。
没有什么比你3岁的孩子把脸靠在你的脖子上更能把你拉近与神的联系。尽管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无尽的菜肴,疯狂的叫喊快点穿上鞋子我们迟到了,家庭作业导致了崩溃-我的女儿们,现在16岁和20岁,把我和更神圣的阶层联系在一起。我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习惯于依偎在我的膝上,看着蜡烛在我身后摇曳。星期五的晚餐;最近,当他们想在深夜谈话时,我感觉到了,分享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而深刻的看法。平展的伸展仍然存在,但这些精神上的闪光却以更大的规律性出现。它们形成了一种可能性模式,一个插件…一些东西。也许是那样某物不是永恒的,但它似乎至少比我自己强。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等到他们成为父母后再经历精神联系,或者直到他们找到其他通往神圣感的入口。希望为他们提供一条更直接的道路,让他们感受到宗教所能提供的归属感,我成了一个朋友所说的“儿童犹太人”,我加入了我城市附近的犹太教堂,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教徒,所以不像钻石镶嵌,我小时候参加过的神殿里的一些头发戏弄的成员,感觉不错。人们赤脚走路,穿着牛仔裤,在我女儿的希伯来学校班级里,白人孩子是少数。
只有一个问题。
这地方看起来也一样,好,宗教的.我考虑换到工人圈——显然是世俗的,关注社会正义——但我意识到在一个汤厨房做志愿者也有同样的目的,帮助我的女孩学会服务他人,但不提供获得灵性的途径。我感觉到了推挽,希望他们以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体验宗教,然后,当我们把脚趾一伸进去就拒绝它。当学校和其他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必须付出点什么,正式的犹太教育结果是非常容易脱落。
仍然,我们每周五晚上点蜡烛,庆祝所有的大联盟节日;我们做了锁在光明节的时候,把面包屑丢在罗丝哈珊的水里,在逾越节的逾越节的逾越节家宴上加上木偶和饶舌乐(爷爷翻了翻白眼问什么时候结束)。我把我的女儿们带到家庭服务中心去度假,如果不是站起来坐下来,他们可能已经睡着了。
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从不祈祷。
当我和孩子们谈论上帝的时候,我的句子通常以“有些人相信……”开头,他们不可避免地问我相信什么。大多数时候我说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火花,联系他人,我们越是敞开心扉,就越能感受到它。祈祷是一些人发现自己内心火花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向他人发送爱之网的方式。
当我的朋友们让我为他们的女儿祈祷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送出羊毛线,这些线和许多其他人的线编织在一起。这些纤维形成了一个毯子,强壮温暖,把他们包围在爱中。当梅丽莎的脑部扫描显示阿尔法波的最初迹象时,当她睁开眼睛时,当她拥抱妈妈和爸爸的时候。当她独自呼吸时,它拥抱了他们,她说了事故后的第一句话,独立行走;当她离开康复中心回家的时候,它承载并支撑着他们,学校、生日聚会和游玩日,为了一个新的正常人。
我女儿曾经问我祈祷让梅丽莎活下来,让她变得更好。“大部分医生和护士都这样做了,”我回答。“但也许。”
祈祷对我来说永远都是不自然的,或者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不再忽视它散发爱的力量,如果不让别人活着的话。我仍然只有一个脚趾,与宗教分离,却暴露在火花中,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触摸圣物。
标题图片通过katerina sisperova/istock/getty images 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