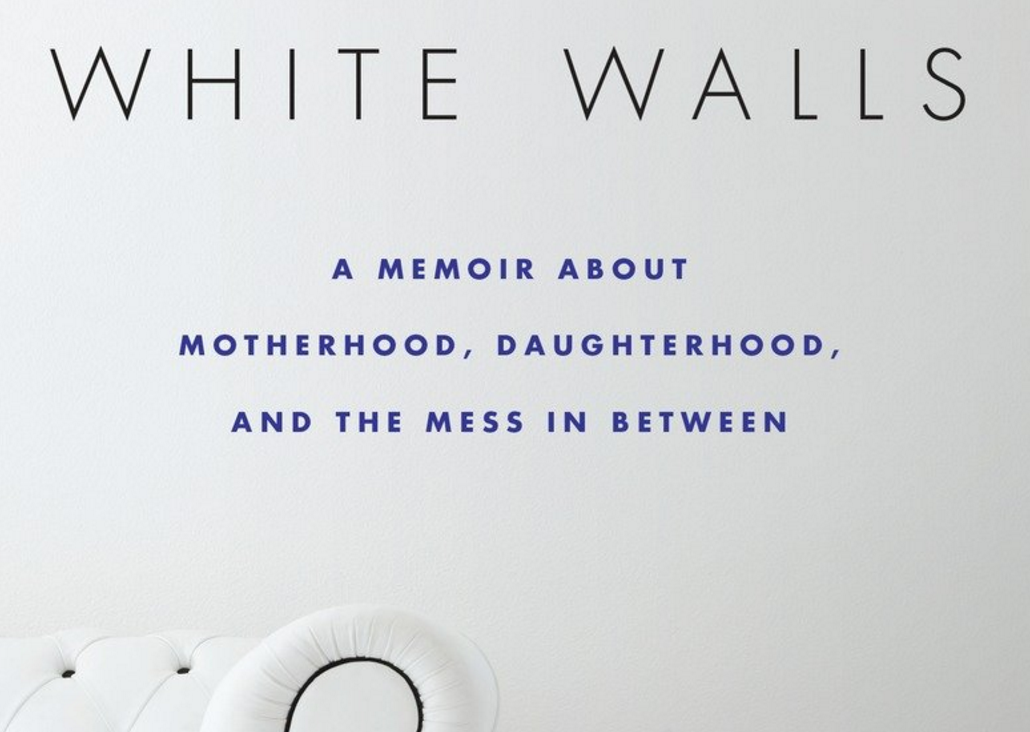朱迪·巴塔利昂的新书,“《白墙:母性回忆录》,Daughterhood以及两者之间的混乱“是对大屠杀的敬意,心理健康,以及犹太家庭的复杂动态,因为这是一本回忆录。通过编织她自己怀孕的故事,让她在童年和年轻时的生活一览无余,官网下载beplay体育ios版巴塔利昂把我们带到她的世界,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孙女,她的家庭的挑战性的过去是如何直接影响到她自己成长的家庭。
虽然巴塔利昂的家人与她母亲的重要囤积斗争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仍然发现自己对巴塔利昂发现的许多揭露表示赞同。作为生还者的同父异母,以及曾参与过心理健康斗争的人,“白墙”把我拉进去,给了我一些答案,但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
我认为,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有些共性是伴随着曾是/曾是大屠杀幸存者的祖父母长大的。我的母亲是在我的祖父母在一个流离失所者集中营见面后在德国出生的。我祖父在集中营中的份额很可观,最终从达豪解放出来,而我的祖母和她的家人逃到波兰的森林里,靠住在地下掩体和极其关心非犹太人的谷仓里生存下来。这一切的后果都是由于我的家庭焦虑。
你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多少,你认为你能追溯到大屠杀的暴行?

我们有焦虑,太!囤积,顺便说一句,通常伴有其他精神疾病:焦虑,大萧条,甚至偏执狂。
虽然我不喜欢,不会提出具体的原因和影响索赔,大屠杀似乎促进了我家人的许多行为。我母亲出生于1945年,在我祖父母从西伯利亚回波兰的路上,在贾拉拉巴德的一家换班医院,Kirgizia。她出生在“家”的路上(想知道家里有没有其他人活着),但是没有家可以回去;在知道家里是什么之前,她是个难民。
适当地,也许,我母亲(和布比)是囤积者,为自己筑巢,紧紧抓住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特别是他们的家,非常害怕一切会突然从他们手中夺走。小时候,我发现妈妈的垃圾堆在我们身体和情感之间被封锁了(当我做噩梦的时候,没有空间爬到她的床上)。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可以看到对敌人的封锁(纳粹,极点,等等)说得通。
顺便说一句,你看到去年夏天发表的一项研究说大屠杀后的创伤是遗传的吗?焦虑实际上改变了基因。我知道这项研究受到了批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想。
你有没有跟你妈妈提过她的囤积和父母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她是怎么想的?
我和妈妈正是通过我的书和我的作品开始讨论她囤积和焦虑的根源。我收到读者的电子邮件,尤其是第三代幸存者在他们的家庭中处理过类似的问题(在一些可怕的情况下,亲属自杀)。我和我妈妈谈过这些,她会简短地回答,通常说一些类似于她在“今日秀”上所说的话:她之所以坚持下去,是因为她太担心事情会被夺走。我祖母也是。
说到大屠杀,我们很快就要讨论转录和分享幸存者的故事的必要性,但善后的故事呢?我们怎样才能更容易接受谈论这类事情,尤其是当幸存者一代死去时,但这一代人仍然感受到了影响?
对,我对此非常强烈。我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中上层阶级,过度受教育,城市环境每个人都在服用帕罗西林或目前流行的抑郁症和焦虑症药物,然而,在犹太社会,严肃地谈论严重的精神病是非常禁忌的,即使我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真的很受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我曾经读到,创伤需要四代人才能通过一个家庭,这完全引起了共鸣。我是第三代;大屠杀影响了我很多天,因此,影响我抚养孩子的方式。
你知道的,我是尝试与犹太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合作,很难协调。有那么少。我应邀在北安大略心理健康会议上发言,但到目前为止,犹太社区里没有。
我想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尤其是战后移民到这里的人,有一个坚定的移民的理想,即不要表现出你的弱点。但是这样做,这使犹太人在精神疾病的斗争中成为一个盛大的话题。当我最终被诊断出焦虑时,就像“什么?焦虑实际上是一种能让你身体极度不适的东西,而不仅仅意味着成为一个忧虑疣?“
我还没有告诉我的朋友我被诊断出患有焦虑症,每天都有药物治疗。我不确定她会“明白”它,你知道的?
对,完全地。我认为还有一种幸存者的负罪感,在不同的世代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当布比躲在女修道院里时,我怎么能抱怨担心物理考试/浪漫约会/在学期前分娩,闲聊的纳粹分子,游过河流拯救她的生命,然后在从西伯利亚到波兰的途中生下了妈妈,发现她的家人被谋杀了?
再一次,我确实觉得我成长在一个人们过分抱怨事情的环境中…就像焦虑无处不在,但从未表达和探索过。
了解更多关于朱迪的信息,她的家族与囤积斗争,更多的白墙“出去!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