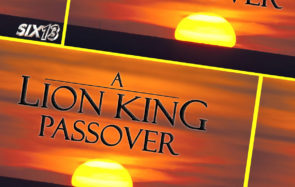这篇文章是的一部分在这里。现在论文系列旨在消除心理健康治疗的污名,改善纽约大都会青少年和家长的治疗和支持。ios下载beplay
今年秋天,我发现自己在急诊室,诅咒一个社会工作者,在“矩阵”里大喊大叫。
坚持E.R.所有真正的病人都被清除了,演员们的唯一目的就是给我上一课,作为对我罪行的惩罚。
我深信自己是一个反社会者,无情的疏忽导致了我工作的医院里许多病人的死亡。
哭着说有人要绑架和杀害我的儿子以牙还牙。
求我丈夫在有人删除我们婴儿的所有照片并抹去他存在的证据之前拯救我的笔记本电脑。
在淋浴时用毛巾系上套索,不要用它,但仅仅是在意识到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都串通一气地和我捣乱之后,才勃然大怒。
医院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安全拒绝我使用笔后,用紫色蜡笔疯狂地在我的日记中乱写阴谋论,套索事件之后。
这一切都发生在罗什·哈沙纳和约姆·基普尔·斯麦克之间的青年党身上,当时正值忏悔的十天之际。犹太人应该互相请求宽恕。我相信我整个犹太社团都恨我,并密谋在赎罪日之前测试我是否会向他们所有人忏悔。
所有这些肯定都无法从快乐中辨认出来,平静,我通常向世界展示的有能力的图像。过去的一年是一个里程碑和变化:新博士,郊区的新房子,新犹太教堂和担任犹太教堂董事会副主席的新角色,为我的孩子们开办的新学校,新生婴儿而且,最近,作为一名军事癌症患者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新工作。32岁时,我拥有生活中我想要的一切:一个充满爱的丈夫,三个健康的孩子,一个由朋友和家人组成的庞大网络,金融稳定,漂亮的房子,一个紧密结合的犹太社区,由一个非常温暖的拉比家族领导,以及一份在情感上要求很高的工作。我是那种生活在facebook上看起来非常完美的女人之一。苹果beplay
然而,八月回来抑郁开始模糊我的思想,就像一团雾慢慢地卷进来,直到它这么厚,我看不到前方或后方的任何东西。从工作开始。我陷入了自我怀疑,被冒名顶替综合症弄得残废。医生和护士在找我帮助他们绝望的病人,我——一个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全新的心理学家——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我的大脑感到迟钝和堵塞。我食欲不振。我每晚睡三个小时,醒来时充满恐惧。
我认识到这些迹象是因为我以前经历过两次抑郁:在哈佛大学一年级开始的时候,然后在大学毕业后开始我的“真正的成人生活”。第二集已经过去十年了,在其间的几年里,我试着假装两件事都没有发生过;甚至心理健康提供者也容易受到侮辱。
第一次发作的药物治疗很快就解决了,我把它归结为向大学压力过渡。第二次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就勉强度过了难关,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心理健康帮助,部分原因是我不想承认自己得了复发性疾病。如果我不寻求治疗,那我就不会接受诊断了,我的抑郁症不会真的存在。
这次我不能否认。我有三个5岁以下的孩子,以及大量重病患者。幸运的是,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关于抑郁症的个人和专业知识,以及十年多的生活经历,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找到了一个精神病医生和一个治疗师。我吃药了。我请假了。我告诉我父母,丈夫,和几个朋友发生了什么。
但几周过去了,而且抑郁症也没有好转。相反,情况越来越糟。然而,起初症状每天晚上和周末都有所缓解,当我和家人在家的时候,现在它们变成了常数。没有逃脱。我忘了不沮丧是什么感觉,我无法相信,我的一个不沮丧的版本曾经存在或将永远不会回来。了解母亲抑郁对幼儿的有害影响,尤其是婴儿,我开始相信我每天都在伤害我的孩子。我开始感到更加绝望。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就在Rosh Hashanah前面。
在星空下的室外赛利卡特服务中心,我听到了我的拉比关于忏悔的信息,相信他是直接跟我说话。一周后,在沙巴特早上的犹太教堂,与我的社区成员的每一次交流都充满了讽刺,可恨的意思。当我环视房间时,我的头嗡嗡作响。基德什感觉每个人都在谈论我。就像一个活的噩梦,无论你走到哪里,有人想伤害你,你无法逃脱。
我告诉我丈夫我们社区对我的阴谋。他打电话给我的治疗师,谁告诉他我的抑郁症变成了精神病性抑郁症,建议他直接带我去急诊室。我默许了,如果只是出于绝望才逃跑。
我在急诊室呆了48小时,编造更狂野和更狂野的阴谋理论。我的房间和急诊室走廊里充满了隐藏的“线索”,我试图向我丈夫指出,当他用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解释来反驳每一个问题时,他越来越沮丧。
他求我按医生的建议去做。看到他的痛苦,我同意自愿住院。我坚决否认自己有精神病,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很不对劲,我需要帮助。
在医院呆了12天,我的大脑开始恢复了。我每晚都服用镇静剂抗精神病药物,这帮助我进入了11个小时的深度睡眠。我一天吃三顿方便饭,恢复了我抑郁时减掉的12磅体重。我参加了艺术疗法和小组疗法以及“运动疗法”,其中包括由穿着铅笔裙的艺术疗法研究生带领的伸展运动。我甚至让妇产科的医生来取我7月份得到的一个宫内节育器;我不明白原因,但我的精神病医生建议,我向我丈夫保证我会遵守。
每天都有家人来访: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涂色,和我的兄弟姐妹玩棋盘游戏,吃了我母亲在家里做的节日餐,她用Ziploc容器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亲切地送来,从沙拉到汤再到我最喜欢的苏克甜点,一切都考虑周到,七叶树。在幕后,我父亲是医院附属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每打一个电话都能确保我得到最好的精神病治疗。
慢慢地,幻想开始消失。每天,我的精神病医生都会把我的症状清单写下来,答案也逐渐变了。不,我已经不在矩阵里了。不,其他病人没有给我传递隐藏的信息。不,我不相信我的精神病医生是任何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答案都是真的。我隐瞒的是,我仍然相信犹太教堂里有某种阴谋。不管那天发生了什么,我都觉得是这样真实的,当然,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空虚的感觉呢?”
我仍然感到内心空虚。每天早上在医院,我醒来时的恐惧和绝望,与八月以来折磨我的一样。希望我没有醒来。相信世界上没有我属于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在精神病房里,我无法摆脱我头脑中的恶魔,我还能去哪里?
“看,”我终于告诉我的医生。“我已经尽我所能治愈了。医院里不会填补这个空缺的。她同意在几天后解雇我。听到我要回家,我全家都松了一口气。我在医院的最后一晚,拉比来访了。我小心翼翼地向他打招呼。
我离开了医院,不再是精神病患者,但仍然非常沮丧和怀疑。一想到要面对我犹太社区的任何人,我就非常焦虑。但是在医院的12天教会了我,你不能逃避你害怕的事情。最好的出路总是通过,罗伯特·弗罗斯特说。
出院后两天晚上,拉比和他的妻子在他们家的星空下主持了一个苏克人的演唱会。这似乎是让我重新进入社区的最好方式,那将是黑暗的,我们会唱歌,我不必和任何人尴尬地交谈。应我丈夫的要求,在我的允许下,一封发往社区的电子邮件解释说,我因精神病症状住院,他需要帮助解决吃饭和睡觉的问题。谁知道他们现在对我的看法。但是最好的出路总是通过.
我一到,我能感受到我的拉比和他的妻子的温暖和真诚的关怀。我从会堂里的其他人那里感受到,也是。在那一点上,我确信这些人不是想伤害我的人。在星空下,那次聚会是药物和精神病学家做不到的:它清除了最后残留的不仅仅是精神病,但抑郁症,从我的大脑。那天在犹太教堂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这是真实的。我觉得我的心充满了深深的爱,连接,感谢他们。我属于这里,和我的家人和社区。
我知道我感觉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那一周,我第一次问我的精神病医生我出了什么事。她回答说:“我要和这个古怪的风暴模型一起去。”“你停止了护理,你有宫内节育器,你在产后一年内,所以你的荷尔蒙在燃烧。你开始了一份压力很大的新工作,你很沮丧,你已经一个月没睡觉了,睡眠不足会使任何人精神失常。所有这些都把你推到了边缘。”
因此,似乎有一个激素和生化的解释,我的症状和医疗解释,我的恢复。然而,还有更多。我觉得我的灵魂在我沮丧的整个过程中,我只注意到它不在的东西已经消失了,尤其是在精神病的最后几周。现在它已经还给我了。

这篇文章是这里,现在系列,旨在消除心理健康的色素,
并由尤加联盟纽约和犹太人委员会.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rojectherenow.org。.